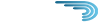张氏火丁
我喜欢张火丁。开始因为她的长相、气质、唱腔、气场、孤独感、不合群……到后来,没有原因了,只因为,她是张火丁。
开始喜欢程派,的确和她有关——她唱的程派,是倪云林的山水画,清极了,简极了,枯极了,可是,就是让人心动。她的长相冷,人也冷,可是冷中的眼神却是善良的。张火丁每张照片都有温存和善良,一个人的眼神是骗不了人的。她不妖不娆不媚不俗,从长相到气质。有人唱程派,可以唱成“长三”堂子的味道;有人唱程派,唱成富丽牡丹。只有她,不浮在哪里,老老实实地唱戏,一张嘴,可以听得到秋天的树叶纷纷扫起,心里是凉的,眼里是凉的,可是,分明又有着心疼在那里,揪心的,动情的——一刹那,就可以落泪。
后来知道张火丁从廊坊出去,开始唱评剧,就是张爱玲说的“蹦蹦戏”。于是没事的时候就去廊坊评剧团转转。廊坊评剧团在广阳道上。早散了摊子,一片荒凉。那院子里还有梆子团,偶尔听到有人唱梆子,心里酸楚的不行——戏曲的好时候过去了。但知道张火丁曾经在这里,心里暖了一下。
也听人说起过张火丁种种,并不往心里去。喜欢一个人,连她缺点都喜欢,何况没有个性的艺术总难成大气。她的个性就像她的名字,怪极了。她本名叫张灯,后来把灯拆开了叫火丁。灯字本来就怪异,拆成火丁就格外怪异。三个字配起来,居然生来奇异的美感了。想起宋微宗的瘦金体,支支楞楞的怪,可是,就是好。
后来因缘际会也去中国戏曲学院教学,与张火丁同事。但未曾谋得一面。即使遇见了,也未必热络得上前打招呼。喜欢一个人,藏在心里就好,她那时离开中国京剧院,去中国戏曲学院教程派,学生叫婵娟。
听张火丁的戏大多是在网上,亲到现场并不多。一是她演戏不多,少而精。上海天瞻舞台贴出演出海报,一天之内可以把票卖完,在中国,只有张火丁有这个本事。我去上海一些大学讲座,遇见上海一些闻人,她们俱是张火丁的戏迷,她们说张火丁:“她一出场,就觉得全场只有她一个人。”
她性格独特,与人来往少。但对戏的痴迷让人敬佩,她是赵荣琛先生弟子,为学戏又跑到南京拜访新艳秋,新艳秋在戏曲界颇有争议。可是,她不怕。只要戏唱得好,她一往而前。这倒像她,不热络,任凭别人评说——有一次和她的琴师赵宇吃饭,赵宇说:“没有听过火丁说过任何人,她只唱她的戏……”
又因为机缘,跟随裴艳玲大师一年多,写她的传记。伶人之间的恩怨听起来让人浑身发冷。其实任何圈子都是一样。裴先生对张火丁有体惜,而且相当喜欢。说起张火丁,先生说:“火丁是真唱戏的人。”裴先生极少肯定人,一语出了,便惊四座。
又有戏友老曹,迷恋张火丁到疯狂。有一日喝高了,哭着说:“您如果让张火丁出来唱戏,我给你磕一个。”我没有告诉老曹,唱戏与否并不重要了,把人生活好才重要。张火丁久不出来唱戏,但她还是会回来唱戏的——一个人,只要学了戏,就让戏附了体,她离不了,这东西是鸦片。就像写字于我,半年不着一字,但一写起来,深深情情,还是这个款这个式,九曲十八弯,哪里能绕得开?
有一次和傅谨老师谈起火丁,俩个人都颇多感慨。但骨子里的喜欢是一样的,张火丁的气息和气质,恰恰和程派一脉相承。悬崖老梅,枯清自赏。至于别人赏不赏,她无所谓。
夜深人静的时候,喜欢听张火丁的戏。可以把孤独放大,那体积明显是侵略内心了。此刻,可以无所顾忌地落泪了。只因此中可以落泪。手机铃声是张火丁的《春闺梦》,每每响起“去时陌上花似锦,今日楼头柳又清”时,总是感觉自己是那个陌上等待夫君的女子,这样想的时候,便觉得凡俗的幸福是多么好。张火丁嫁人生子,很多戏迷曾经感觉寂寥,我却为她庆幸,生活才是大戏,她应该有的幸福早来的好。
恍忽多年前,在戏院里看张火丁,她正年轻我正年轻,台上是她舞着水袖唱《荒山泪》,台下是我为戏黯然惊魂……多少年过去了。回首刹那,人书俱老,她的声音亦老了,前几日她灌了一张CD,声音大不如前。可是我觉得刚刚好,一个人的声音老到沧桑,再唱那低回婉转的程派,如果是隔了多年她再出来演上一场,想让人不落泪都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