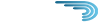父母的养老
父亲握住母亲的手,是轻轻握住。平时他的手因病会不停抖动,但那天不抖,整个的一只左手,稳稳地握住母亲躺在床上伸出来的左手的无名指,握得长久。
那天,母亲说:“我们去养老医院。”
有没有听错?
94岁的母亲,为自己,也为92岁的父亲,提出此愿望。
我们一起面对现实:父亲的帕金森病让他行走艰难,生物钟日夜颠倒,一不小心还会在家跌倒,有时跌出血,好在没伤到骨头。母亲脑健,但心脏偶感不适。他们要将自己完全交付给一个陌生的环境,摒弃家人全天候照顾。母亲坚信,养老医院必有负责任的医生和专业看护,更有利于他们鲐背之年后的“安身立命”。更重要的,母亲说:他们的幸福,绝不能再建立于后辈艰辛的劳累之上。
父母亲相濡以沫,情感深厚。父亲初听去养老医院,有点被惊到,心惴惴,但之后对母亲说:“你去,我去。”
终是去了。
入门不适的是父亲,知识分子的他觉着“自由”突然失去。因怕他摔倒,不能随意走动,倘一人行动,护理的阿姨会惊呼阻止;睡觉的床有高高围起的护栏,他视之如手铐脚镣,火气忒大,对其踢打,以致血压攀高;还抱怨晚上给他使用“尿不湿”,指斥阿姨态度“法西斯”……
此时,我们四个子女是伤感的,自责的,互觑:将父母送来此地,错了?
感谢母亲,一如从小对我们的理解、大度和照护,现在依然那么思路清晰通情达理:“沒错的。决定到这里的,是我们自己。环境适应,需要时间。”她只是要我们子女有空就一起去为父亲做“心理按摩”。
我们常去探望。
那天,我带父亲到养老医院隔壁一间房,见到一位背很佝偻的老太。她曾是大学老师,84岁。一问,竟不是病人,是病人家属。每天家里、医院来回,风雨无阻,服侍精神失常病痛住院的88岁的丈夫。一个人,几年如一日。她贴着父亲的耳根说话,很柔声地请父亲安静:转变自己,面对现实,想自己的幸福,认识到子女出于无奈也出于孝敬,将他送到这里。她说:“我也想进住养老医院,但没床位,身体条件不够格。但我必须天天来。”父亲仔细倾听,“你讲的有道理”。之后,抱怨减少,似在慢慢平复心情。
再一日,我去看父母亲,给他们吃我在家里煮好带去的鱼香肉丝面。父亲说好吃,母亲也说好吃。他们吃我煮的面,我吃他们在养老医院食堂烧的赤豆粥,肉饼子炖蛋,冬瓜,还有大骨头汤。然后我推父亲的轮椅到楼下花园廊道,和他谈心,去运动小区,给他看运动器材并做示范动作,父亲竟垂下眼睑打鼾了。我赶紧将他推回病房。觉醒了,他精神也来了,自己走路,我在一边微微搀扶,他甩开我的手,碎步挪到一墙之隔的母亲病房。父亲说这样才好,动了,锻炼了。母亲说你一个人不能走路,摔了不好。父亲反过来说母亲:“我看见你倒着走路了,这年龄,不能倒走的。”那天他们两人说了许久的话,都大声,都耳背。
其实入院前,医院给父母检查,告知母亲,虽然你年纪大,但状况不错,可以不住院。母亲摇头,指我父亲:“他脾气大,胆小。我不在他身边,不可能。”一次,父亲又闹情绪,吵回家。父亲问母亲:“你到底怎么想?”母亲平静如止水,轻拍父亲脸上几根银白的拉碴胡子,“你回家,我就一个人住这里。这是我现在和以后的家。”父亲口木然微张,低头,无语。
转身,再下一个镜头:母亲正手拿一个他们都爱吃的小羊角面包,将其一小块一小块撕下来,送到父亲嘴里。
一切都不易。
那日,父亲大解,护理阿姨不在,我给父亲擦洗。过程从生疏到圆满完成。父亲突然说一句:“儿子,你是第一次帮我擦洗。”我内心猛一惊。而在给父亲擦洗时,又有新大陆发现:在稀落的毛发下,他后颈上露出一大块暗红色的胎记——愧死了,父亲92岁,我才第一次看到这个隐藏的胎记。
意外和不幸,有时就在一切看似晴朗的日子里突降暴雨倾盆。
几个月的精心护理,父亲在养老医院没一次跌倒,生物钟的日夜颠倒也大为改观——因为心情放松睡眠好转。“一片大好形势”下,那天清晨医院传来的消息,则让我们所有人遭受闷棍似的重击:不是父亲,是淡泊乐观的母亲,在医院病房内意外摔倒,股骨骨折了。
所有家人一起急速赶往。
见到了痛苦的母亲,见到了好像做了错事一脸歉疚的母亲,说是她大意了,真大意了,两只手握两件东西,一个茶缸,一个水瓶,没支撑,转身一滑,轰然倒地了。和护理的阿姨无关,更和护士医生无关,就是她一个人的错。
所有护理她的护工、护士、医生,在一边都红了眼眶,不仅仅因为她们获得母亲的"百分之百无责证明"。
惊动了父亲。他过来,看着躺卧床上的母亲,厉声问我们:“为什么所有人都围起来看她?”
母亲骨折后的两天,即刻去专业医院动大手术,换一个髋关节。全身麻醉。这是必须要过的艰难的坎,对94岁的母亲。她坚决地要换回一个健康的自己。但所有人极度担心。
最初的方案是选择保守治疗,母亲闻之点头。转瞬医生一致推翻:唯有手术,才有康复可能。母亲闻之再次轻点一下头。但要求我们术前术后对父亲都“封锁消息”。母亲对我们说过,“我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现在,我们又一次见识到母亲积极的镇定,所有最终的风险性选择都一概自己承受,并迅速坦然面对。开刀医生术前一句话,“这开朗健康的老太太即便100岁,我也敢为她主刀”,让我们始终对母亲保有乐观和信心。
五天之后,母亲终于回家,回养老医院的家。此刻,她才将发生过的所有的紧张不安和承受的肉体痛苦,有点撒娇意味地尽情吐露给我们,唠唠叨叨长达几小时。
开刀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忘记了独自一人在养老医院的父亲,而养老医院的护理人员说,父亲那几天的“表现”,出乎意料地好,不来气,安静,饮食佳,配合度高。
父亲和母亲的“劫后团聚”,没有太多动人场景。不流眼泪,但有握手,相看两不厌的样子。父亲握住母亲的手,是轻轻握住。平时他的手因病会不停抖动,但那天不抖,整个的一只左手,稳稳地握住母亲躺在床上伸出来的左手的无名指,握得长久。然后我们请父亲坐定在母亲床右边。这时换成母亲的右手,从被子里伸出来,很自然地罩握着父亲的左手。
再过一段时间,是秋日的一个午后,我推着轮椅,和父亲来到养老医院的花园。父亲很满足,说:“阳光好,桂花香。”又说,他其实早就清楚母亲动了大手术,“你们以为我不晓得?我可是长时间在大医院里做的……”
哦,这桂花的醇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