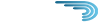打不碎的鸡蛋
打不碎的鸡蛋
马莱巴
一只帕多瓦种的母鸡,在靠近帕尔马城的一所农庄里出生长大,它有个毛病:生出的鸡蛋的蛋壳很容易碎。原因在于其它的母鸡都吃小石子和石灰微粒,所以:它们生下的鸡蛋壳都结实;而它只吃小麦、高粱和玉米粒,或者吃小虫子,它吃的虫子有玫瑰色的、黑色的和其它各种颜色的,它从来不吃小石子和石灰微粒,因为它消化不了。要是偶然吃下去一颗石子,那石子就整天呆在它的胃里了,而且使它整夜合不上眼,所以,它生的鸡蛋壳很容易破碎。
一天帕多瓦母鸡听到一位卖鸡蛋的商人对农庄的女主人抱怨说,有一只母鸡生的蛋太容易破了,每次运输途中都得碎。母鸡听了十分担心,因为它知道,一旦女主人发现了那些蛋壳易破碎的鸡蛋都是它生的话,那么很可能就会把它宰了。农庄附近有一家大理石匠铺。一夭,母鸡试着去尝大理石粉末。石粉既不好吃也不难吃,但跟小石子和石灰微粒一样难消化。第二天,它生下的鸡蛋蛋壳呈大理石的颜色,外表十分好看,但还是很容易打碎。另有一天母鸡从石匠铺面前走过时,看到有一桶罐子打开着,上面写有“硬化剂”的字样。“但愿这东西没有毒。”可怜的母鸡自言自语道。母鸡在那白色的糊状物上啄了两三下,原来那是石匠用来粘大理石的粘胶。它随后跑回到鸡舍去,因为要是吃了那东西要死的话。它情愿死在自己的窝里也不能死在马路上。它久久地睁着眼睛等着肚子作疼,最后它睡着了,它一夜睡到大天亮。黎明时它生了蛋。
它不像往常那样啼叫以通知女主人来取蛋,它拿了鸡蛋到一片树丛后面去。母鸡先用嘴啄,然后拿一块石子敲:这一回,它生的蛋可真硬,于是,它就把鸡蛋放回鸡舍去。
帕多瓦母鸡生下的蛋在运输途中没有破碎,它被放在市场的货摊上,让一位工人的妻子煎鸡蛋吃。女人回到家,把所有鸡蛋都在碗边,她拿起帕多瓦母鸡生的这个鸡蛋在碗边一敲。但鸡醚有打碎,碗却打碎了。“咦,真怪!”女人自言自语,她拿起鸡蛋,在大理石做的桌子角上敲。大理石被敲掉了一角。她拿来了锤子,试着用锤子敲鸡蛋。还是敲不碎,于是她把那只蛋放在一边,因为她不好意思对丈夫和儿子说自己连一只鸡蛋也敲不碎。
丈夫与儿子吃了用三只鸡蛋煎的蛋,而不是四只。妻子说人家卖给她一只不新鲜的鸡蛋,也许已经坏了,所以她故意没煎进去。
第二天,她那个大学生儿子把几寅烂西红柿和那只鸡蛋放进包里,因为那天有部长来参观。那个部长诡计多端,他想与大学生们见面,让他们鼓掌欢迎。大学生们商议好给予他应有的欢迎。当那位部长一出现在学校门口时,烂西红柿和臭鸡蛋朝他劈头盖脑地扔过去,那个工人的儿子瞄准了部长,把那只敲不碎的鸡蛋朝他的前额扔过去。只听见“啪”,像是打过去一块石头似的,部长应声倒地。大家把他抬出去,用冰水袋敷在他的额头上,因为部长的前额正中长出一个大鼓包。尽管用冰水敷,他那个肿包越来越大,活像犀牛的角。
打从那天以后,部长再也不接见大学生了,也不再去参观什么开幕式了,因为不管怎么冷敷和治疗,部长额头上的那块包怎么也消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