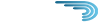火鸡
昨天下午去幼儿园接小虎子回家,去的早了些,一条长龙般的队伍全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接小孩的大多是爷爷奶奶,老年人们心情焦急地等待幼儿园开门,就在这时过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她的出现一下子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不是因为她长的天姿国色,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而是因为她顶着一脑袋颜色,她的头发梳成一缕一缕地,每一缕都泛着金属光泽,且是多种颜色组成,大致上看似乎是由水红、深蓝、鹅黄三色构成。大家议论纷纷,而我直接就想到了郭达和蔡明合作的小品《相亲》,于是我脱口而出——火鸡。
站在我后面的一个长舌妇立刻就大声地把我的话转告给那个年轻妇女,她说:“你听到没有?那个老头说你是野鸡。”
我一下子叫苦不迭起来,这火鸡与野鸡可不是同一品种,火鸡是食物,说某个女人是火鸡充其量就是郭达表达的那个意思,让人眼花缭乱,没有太大的贬义;而野鸡是娱乐品,是妓女婊子的别称,倘若那个年轻女人跟我顶起真来,搧我两个摸逼耳光,我岂不是没有好相哭?即使女人打了你你也是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谁让你为老不尊先骂人家是野鸡来着?
好在那个年轻女人没有自己接过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她说:“我听见了,大爷说我是火鸡,年纪大了,奥克了,他不识货,我这头发是论缕计费的,一缕一百块,就我一脑袋头发好几千块。”那个意思是不跟我一般见识,也不责怪我。
长舌妇不甘寂寞又说话了:“哎呀!我的妈呀,就为几根逼毛花几千块呀?你的钱是从天上流下来的,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花这个冤枉钱。”
那个年轻妇女说:“你的逼毛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呀?大冷天也不怕冻着。”
长舌妇不吭气了,说起长舌妇我对她略知一二,按说也是一个苦命人,是从附近农村嫁到工厂里来的,只是她没有选对丈夫,刚怀孕丈夫就因盗窃罪被判刑,孩子出生就没见过父亲,也不知那些年她是怎么过来的?丈夫坐牢去了,自己又没有职业,母子俩生存就成了大问题,也偷过汉子,也卖过淫,总之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她对丈夫还心存希望。有时候用挣来的血汗钱给丈夫送几件衣物,有时候送食品和香烟,她希望丈夫刑满释放一家人再度团聚。
可是,她丈夫在监狱里再度犯罪被加刑,最后死在监狱里了,长舌妇干脆豁出去了找了一个老光棍回来同居,老光棍也不要孩子就把长舌妇的儿子抚养成人了,长舌妇如今也算苦尽甘来,儿子在一家外企当员工,据说一个月能有一万多元收入,她也跻身于奶奶行列,因为她特别喜欢饶舌,本来应得到人们同情的,但是大家都不爱搭理她,我今天就差一点被她坑了。
幼儿园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孩子们鱼贯而出,小朋友也见到了那个年轻妇女的头发,他们竟然跟我一样脱口而出——呀,火鸡!火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