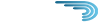永远的绯红
我当过多年的医生,听到过外国同行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美丽的女人得了不治之症。治疗本身更加重她的痛苦,延长她受苦的时间。我实在是受不了。她对主治医生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求您了,我的意志已经走到尽头。除了消耗别人的精力与财富以外,唯一的用处就是感受痛苦。经过郑重的考虑,我恳求您帮助我,结束生命。
您是说,要我助您自杀?医生惊异地问。
不需要您亲手来做这件事,我只请求您告诉我应当怎样做。它最好简单实用,像电子计算器的按键一样,只需轻轻一按,一切就结束了。那装置要力求百发百中,您知道,我懦弱,虽然决心已下,但我怕最后的关头会手忙脚乱,意志动摇,手指发抖。还有最后一条女病人突然显出羞怯,说,您帮我选择的死亡方式最好不要使我看起来很丑陋。
女士,您让我想一想,这个问题很突然我钦佩您的勇气和智慧。它其实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但这一切,需要手续。
我现在很清醒,完全是我的自由选择。但是您说得很对,我和我的丈夫将写出书面文件
医生做了一个精巧的装置,类似儿童玩的弹弓。它有一个小小的机关,只要轻轻一揿就会有一支锋利而强劲的针头射进皮肤。它携带着剧毒药液,可在几秒钟内置人于死地。
女士和她的丈夫选定了一个吉日。医生和丈夫随着女人走,他们不知道她要到什么地方去。无论她到什么地方,他们都只能跟随。
就这里吧。女人如释重负地说。她的肌体已经十分虚弱,还要留有足够的劲道操纵小弹弓。
医生突然想丢掉他的小弹弓,让我们再试一试另外一种治疗方案,好吗?一切都重新开始。他满怀希望地说。
女人微笑了,说:当决定把这里当做最后的安息地时,我也动摇了。但是,夜间频频发作的剧痛提醒了我。我的生命已经不属于我,只服从病魔。我按照自己的意志完成了一生,我是胜利者。
她吻了丈夫,吻了医生。
我不得不请你们走了,很抱歉。她说。
祝晚安。这是她的丈夫说的唯一的话。
两个男人踏着厚厚的腐叶向东方走去。
他们没有回头。不知是怕自己失了勇气还是怕那女人失了勇气。
等一等!突然传来女人尖锐的叫喊。
面对医生,她说:我再问您一遍,您一定要如实地回答我。过一会儿,我会不会很可怕?特别是我的脸女人目光炯炯地盯着医生。
不会。什么都不会改变。一切都和现在一样,特别是您的脸,气色很好。一切都将保持住。那将是一种凝固的美。医生冷静地说。
那太好了!快,请你们快走!我感觉到我脸上的血正在往脖子里回流。红色就快保持不住了。我需要这份健康的颜色。她说着用双手托着自己的下巴,以为能够阻止血液的回流。
时间到了。医生说。
再等一会儿吧。万一我不能忍受。丈夫说。
您应该相信我,相信科学。医生率先踏响了冬天留下的黄叶。
女士侧卧在林间的木椅上,脸上留存着永远抹不去的绯红。
那位外国医生,后来被州法院传讯,被控谋杀罪和制造杀人武器罪。
这个案例引起了轰动,许多女人团结起来,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无罪释放那名医生。不久,医生被判缓刑,走出了看守所。第二年,州立法院修改了法律条款,安乐死成为合法的死法。
在美丽和爱面前,法律也让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