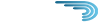生日为她点首歌
门被轻轻地推开,外面闪进一道光亮,操场上噪杂的音乐也随之灌进来。门口,缓慢移动着一个女人的身影。我头也没抬,继续着手中会计催要的报表。
“老老……师,这是政教处吧?你是仲主任吗?”她怯怯地问。
“是,我就是。什么事?”我依旧忙着手中的活,应着她。
“我想麻烦你点事?”她向我的办公桌走近许多。
“我?”我抬起头,面前站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农村妇女,羞怯和执著一同表现在她因紧张而略显呆板的脸上。
“什么事?”我爽快而干脆地说,心想你快点说,我还要处理手中的报表。
“是这样的。”她依旧不紧不慢,似乎在选择着词汇。
我看着她,很不耐烦,想让她坐下,却又决定还是让她站着,好早点结束谈话。
“我刚才到广播室,想给孩子点首歌。她们说不行,学校不允许。他们看我不走,又是从农村来的,就叫我找你试试。”她似乎看得出我的忙碌,一口气说了一大通。
“学校以前允许点歌,后来学生瞎点,校长就让关了。”我说得也急。
“我不是瞎点!今天是孩子生日。我走了几里路,又花十几块钱坐公交——我还晕车,来点歌的。她今年高三复读,再考不上,就没书念了。”她说得有点乱,但很恳切,语气里淡淡的愁绪让跳出农门的我不由心动,眼前浮现出高考前母亲为我煎鸡蛋的画面。
我一边听,一边思考怎么办。
“老师——”她发觉称呼错了,连忙改口,“哦,主任,请你帮帮忙,给我开开后门。”
“哪班的?叫什么名字?点什么歌?”
“高三(8),叫刘艳。点什么就随便你们了。”她如释重负,看我在手边的纸上写着,连声道谢。
我撕下纸,对她说:“我现在就去办,只怕还要挨校长批评呢。”
她看我起身,双手抱在一起,弓着身向门外退。
关上门,我朝她晃晃手中的纸,径直到四楼广播室,把纸条交给学生会的两个女播音员。
“嗯?”我表示反对,接着下着命令,“点一首励志的,你们学生爱听的。”
说完,我下楼到食堂吃饭。
在一楼大厅,我又遇到刚才点歌的妇女,她正竖着耳朵听。看她的样子,我觉得好笑,便走过去对她说:“可能还要有一会才到,要不你先回去,你看天都晚了,反正会播的。”
被我看穿了心思,她倒不好意思起来,黑黑的脸上似乎泛起一层红晕,“哦哦”地应着。
我在食堂吃到第二个馒头的时候,听到广播里说:“高三(8)班的刘艳,今天是你的生日,你的母亲从家里来为你点歌。下面这首汪峰的《勇敢的心》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也预祝你在一个月后的高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我边吃边欣赏着音乐,心里同时涌起一丝被校长批评的担心。
出了食堂的门,天边的彩霞让人心旷神怡。我悠闲地走在校园的大道上,看着成群结队的学生从操场上恋恋不舍地向教室走去。晚自习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想到那张没有完成的报表,倒不再着急,心想,还是暂时享受一下校园难得的空旷吧。
“仲主任,刚才那歌谁叫点的?”他一开腔就是责问,弄得我一时无从应对。
……
“她母亲年前才去世,当时她请了几天假。她母亲现在怎么可能来点歌?现在快上晚自习了,刘艳也不在班上,你看,出事咋办?”
我一听,心凉了半截,没想到好心还办了坏事,而且是个不大不小的坏事。
直到晚上七点四十,我和高振雄才在公交车站找到刘艳和那位妇女。没等她开口,我劈头劈脸就是一句:“你怎能冒充她妈来瞎点歌?”
“我是她三姨。”她解释道。
“什么三姨四姨的,也不说清楚,害得我们找了半天,孩子要是有什么事谁负责任?”
班主任高振雄看我脾气不好,马上把刘艳拉到边上:“你也该懂事了,怎么不说一声就跑出来?”
“我听到歌声,知道不对劲,跑到广播室,听她们一说,估计是三姨来的,就找出来了。忘了跟你请假。”刘艳脸上还明显带着泪痕,接着又伤感地低声说,“三姨说,我妈去世前,叫她今天一定要到学校为我点歌的。”
我和高振雄听了,愣在当场,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泪水已在眼里打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