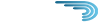打酱油打醋,打出爱情
大排档饕餮完,我找服务员要塑料袋给如意打包,如意按着我手说不用,她包里带着不锈钢饭桶,好几层的,荤的素的主食都能区分开,特方便。在眾食客惊讶的眼神里,打包完毕,如意拎着饭桶悠然上车绝尘而去。
如意就是这样。买啥都自己带家伙什,不用包装,她把这叫“裸装”。
买衣服,不要包装,自家无纺布的袋子提上就走。傍晚要喝的鲜奶,塑料袋装好的她不要,举着老辈子茶缸,“来一斤半”,老板打一斤半,最后添一丁点,如意说这是自带家伙的福利。
那天,如意去乡下摘草莓,不锈钢盆没带,路过胖燕的小菜馆愣是踅摸了个酒坛子,口小,草莓好进,出来可难了,掏,一个一个掏,着急抓一把手得卡坛子口。那天,我们吃了一顿醉草莓,回家都不敢开车了。
我们小时候,很少用塑料包装,大多用纸,买油条,买布,买瓜子,买茶叶,买白糖,都用纸。不用纸就自己带家伙,有时攥一个网兜或挎个篮子,篮子是荆条或者打包带编织的,谁家要是看到塑料袋,羡慕得不得了,那简直太先进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塑料袋成了主要包装,隔水,隔尘,不串味,离开塑料袋的日子简直活不了。
如意活得了,她后备箱都是干净的器皿或者筐。没塑料袋的生活如意也别扭,网上买东西包装都是塑料袋,她就跟客服谈,不用塑料袋行不,人家说路上磕碰损坏不赔,某次买的书到家都成了纸浆。从此,如意尽量去实体店,我说她越活越倒退。
大概每隔一个星期,你都会看到大街上,如意手攥着个瓶子,疾步去槐茂酱菜厂买酱油。我觉得她费事,但如意乐意,说:“有卖散货的,就有自带包装的,怎么啦?”
都说如意这“裸装”的大神一辈子也不会找到对象,可人家偏偏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就是在槐茂打酱油的时候,有个男人,是一家企业的工程师,来打醋。俩人都攥着同一个牌子的酒瓶子,服务员酱油打好,醋打好,放柜台上,俩人自己取,出了门才发现颜色不对,拿错了,互换,搭话,认识,熟络,工程师也是“裸装”拥护者。这样的两个人能吃到一个锅里,爱情萌芽……
我裸妆,如意总挑我毛病。我们的爱好同音不同字,凭啥她看不上我。如意说:“裸装是少制造污染,裸妆是影响市容。”我说我不裸装还拉动内需呢,可怎么说出来感觉也不如她底气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