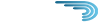我为爱情流过泪
我出生的地方,是辽宁北部的普通小镇,有个杀气腾腾的名字:“调兵山”。传说金国大将金兀术曾在此地调兵遣将。我的家乡原本只是东北寻常小村落,从清末到民国年间都属于其他县域管辖,一直到上世纪因发现大量煤矿而开始逐步建城设县:先有大國企,后有人居小镇,居民除了本地土著,还有大量全国各地迁徙而来为大国企充当劳动力的外来居民,且很早就实现了城镇化。矿山、工厂、医院、学校……乃至政府部门设立之初也要和大国企二元并立,各有运转系统。
小镇并不能算广博深厚的土地与教育历史混合了人类欲望之后共同塑造出家乡人奇异的人格特性:并不出产诗情画意的文艺青年,也不出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的理想人类,貌似更盛产脚踏实地的欲望子弟。家乡人,以更急迫的进取心和拼搏心,携带着来自草根的莽撞和活力在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繁衍生息。
我喜欢的那个男生,是我高中的校友,比我低一届。我是他的学姐。他入校时,我已经读高二了。我们是怎么认识的也记不清了,反正有一阵子总有一个少年默默地跟在我身后送我回家,早晨又等在街口送我上学——这事其实挺可怕的,简直就像美剧《跟踪者》里的桥段,仿佛杀人戏序曲奏响!但其实我被尾随了并不怎么知道,偶尔看到他好像在等谁也觉得蛮奇怪的,“哎呦,好眼熟啊这个男生,哪儿见过,在等谁啊?”大概好几次以后才能把少年和自己做个联系,“妈呀,这人,不会是在……”
等我注意到少年时,他就不再出现了。反正他是很奇诡地默默出现的,在路上打过几个照面,没说过一句话。我们到底是怎么说的第一句话呢?真是记不得了哎!
后来我就住校了,每个晚自习结束都半夜了,每天早起晚归着实挺不方便,父母就让我住在学校宿舍,每周回家一次。当时有个同年级的隔壁班男生正在追我,各种关心各种飙存在感,我刚搬进女生宿舍他就让同班女生来问候,那种毫不低调地示爱也是蛮吓人的——我那个时代的男孩子一点儿都腼腆,青春期的天理正在起作用,男孩子之间的战争其实在十七八岁就已开始!一方面这种追求让人蛮陶醉,一方面也让人害羞和害怕。
我记得我拒绝该男生是在冬夜,他把我从自习课约到学校后面的半山上,寒风凛冽,天寒地冻,简直是杀人戏序曲再次奏响……当天我们两个在操场上打篮球,被同班的坏小子看到,冲我们喊了很令人崩溃的话,某少女当场就羞愧得哭了——当晚该男生就找我谈话,大意是,这有什么好羞愧,给我当女朋友不是蛮好哒?
不好,一点都不好!不乐意呐!
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少女时代到底是个什么调调,可以很放松地和男孩一起玩,但是没办法以女朋友身份和他们当中的某个成为亲密小伙伴——我这种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优秀习惯一直保持了很久很久。
大约是当时,另一个男生也在追我吧?不显山不露水,既不强烈到让人害怕,也总是像一缕春天的小微风,不远不近地,撩着。
相比之下,我那个同年级的男生的爱慕来得太猛烈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大学女生宿舍楼下摆蜡烛的弹吉他的,简直就是裹挟着舆论,汹汹而来,春风十里,吹不死你!
反正小学弟的名字我不知不觉就记着了。我们学校里有个校园广播,每周都出个几次声音,播一点同学们写的“我为祖国献石油”之类的青春文学(请脑补《夏洛特烦恼》里的校园广播),我恰好就是被学校选出来去读幼稚文字的女声优,而恰好恰好就读到了由这个曾经尾随我的小学弟写来的幼稚的小诗。我第一次公开念出他的名字,是在学校广播的大喇叭里……
唉,我的家乡啊,蛮不产出文艺青年,我们那儿的子弟习惯像二人转里演的那样直白求爱,比如追我的那个同年级的男生,会很直率地说,“妹儿啊,给哥当女朋友呗,哥稀罕你!”你拒绝他他也不会又哭又闹又上吊,而是洒脱地笑笑,“没事儿,妹儿啊,你看上谁了,哥帮你追!”
唉,反正我遇到了个俺们大东北“你瞅啥瞅你咋地”气氛之中脱颖而出的文艺范儿,还是小我一岁的学弟。会写诗、画画、唱歌,会用秋水一般波光潋滟的大眼睛深情地、多情地、一直一直地注视着你。
他写过很多很多情书给我。送过我他亲手画的水彩画,是家乡风物,寒冬的松树上站了一只长尾巴的大喜鹊。在我耳边唱过谭咏麟的情歌。送过我命运交响曲、孟庭苇的歌。我高考前一天,他巴巴地跑到我教室门口,手里捧着个迷你录音机(walkman),说,这个给你听,能缓解紧张。戴上耳机,按下play健,是小孟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每年过生日,都送一个八音盒给我。我有很多年,听不得喜鹊叫。听了就想哭。
我高考结束,暑期和他正式约会。他说,我第一次看见你,你正穿过咱们高中的篮球场,我就去问,那是谁?她叫什么名字?我要让她做我女朋友。
说这话时,我们坐在家乡唯一的山顶,并排坐在悬崖边的石头上,他皮肤黝黑又长又健壮的双腿伸在半空,太阳从背后照过来,把一对少男少女的影子印在崖底的草地上。
那年,我18岁,他17岁。
八音盒,依然躺在家乡老房子我住过的卧室的抽屉里。那些情书成摞成摞地挤在一只纸箱里,放在昆明我家书架最顶端的柜子里。自打放进去,我再没碰过那扇柜门。
我们最亲近的一次是某个冬天,他放寒假,我休假,他把我从冬雪的台阶上抱下来,抱在怀里,能听到他胸口里如烈鼓般擂响的心跳阵阵。
我有很多很多次梦见他,梦见他站在类似商场的上升下降的扶梯上,他从上面下来,我从下面上去,我们错身而过。
某次,在睡梦中被哭声惊醒,清清楚楚地听到有人,在一小声一小声地抽泣,心想,是谁?谁在哭?伸手到脸上,发现正在哭的人竟然是我,大波大波的泪水从眼角如溪水般涌出,一直流到枕巾上。
他曾经是那个我无法提起的名字。
我们交往了两年?还是三年?某年夏天,我在福州接了他一个电话,从那一刻起,再未相见。
我最近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从一个完全想不到的人口里,“某某,他现在在某某城市。是当地的地产商。”天哪噜,那个城市,我去过不止一次。他高中毕业在上海读最好的大学,学土木工程。
我们都害怕过早地被某个人标记,一直心怀期待地盼望着更好的将来。留在家乡或者散落在东北各地的家乡子弟,他们当中最优秀、最有才华的青年才俊,大半进了政府部门;而我曾经深爱过的才情少年,他成为地产商!
一想到这其中的种种离奇,简直想要仰天大笑:上天啊,你还真是毫不吝惜地使用我们这些昔日的纯洁的心怀理想的少男少女——在这个诡异的时代,想要过得稍微有尊严点还真没他路可选,我辈当中最优秀的青年们要么汇聚在在政府部门成为食税阶层,要么成为地产商。只能说,我们身上都留下了来自时代的深深的烙印。
东北男生一直对我有着神秘的吸引力,每次看到来自家乡的后生,都觉得对方既性感又陌生,既熟悉又完全看不懂。
我毕竟是个小镇青年哇,曾在小镇得到过人生中最强烈的一段爱情。也是家乡凛冽的冬风和当地人二人转般热烈的地域性格给了我蓬勃的生命之火,当世界的纷繁复杂在眼前徐徐拉开,潜藏在内心的以好奇为燃料的小火苗便如沐春风般左右摆动,必要亲自试试这人世间的每一缕春色、每一缕痛。